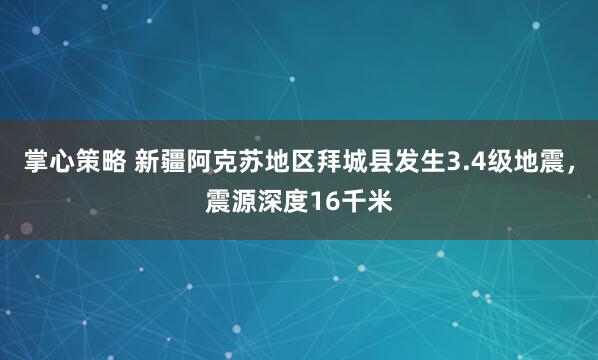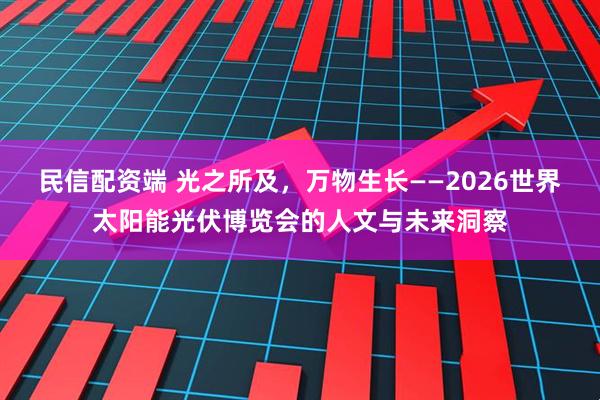1984年年初,我读大三的时候中国星配资,决定报考1985级金融专业(当时叫货币银行学专业)硕士研究生。查阅招生简章,我发现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当时是没有金融硕士学位授予权的。同时,为了准备考试,我开始阅读《金融研究》这样的顶级学术杂志,很快发现,北大有一位曹凤岐老师,是专门研究金融学的,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。由于杂志上的单位署名只有“北京大学”四个字,我无从知道他在哪个系(当时,大学下面一般不设学院),是什么职称。
1985年秋,我入读中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,师从有“北黄达南周骏”之称的著名金融专家周骏教授,攻读硕士学位。在财大的图书馆,我读到了曹凤岐老师发表在《金融研究》当年第9期的论文,《回归分析是测算货币需要量的一种好方法》,所属单位是“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”。后来阅读曹老师的《坦荡人生无悔路》,我才知道,就是在这一年5月,北京大学设立了经济学院,经济管理系是下设的三个系之一,由厉以宁老师担任系主任,曹凤岐老师担任系副主任。这一年也被认定为光华管理学院的起点,虽然北大商学教育的历史要早得多。
1995年秋末,我决定报考金融学专业博士研究生。当时还没有网络,查阅招生简章,必须要到省招办,看一本装订成册的全国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。我跑到省招办,工作人员告诉我,目录被另一位我认识的考生借走了。我又跑到这位考生家里,转借目录(这位考生后来不仅考上了,而且成果丰硕,还担任了《经济研究》杂志的总编辑)。打开目录,翻到北京大学的页面,我发现北大是招金融学博士的,在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下设有金融学方向。但是,这个专业属于一个名字非常奇怪的单位,“光华管理学院”。看到这个名称,我非常疑惑,怀疑它不是正规的北大学院。不过,当看到金融学方向只有一位导师招生,这位导师正是曹凤岐老师时,我悬着心立刻放了下来。
1996年初夏,我来光华复试。第一次来到了老法学楼四层的光华办公地点,也第一次见到了曹凤岐、秦宛顺、高成德等老先生。我觉得,一个学院,能有一层楼的部分办公室,已经相当不错了。当时,我并不知道,光华最初的办公地点,只有一间水房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一年多以后,光华楼(当时还没有老楼、1号楼的说法)就落成了。1997年7月,大楼落成典礼在楼下露天举行。许多师生参加。我记得当时,参会的老师同学都非常高兴,大家的笑容都很灿烂。我也第一次在光华楼里走来走去,兴奋异常。
光华楼的落成极大地改善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办公和学习条件。曹老师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讲座和研讨会。它主办的“经济与金融高级论坛”总共有120多期。光华楼落成以前,这些活动都是先在三角地贴海报,然后在学校的各个教学楼大教室打游击。记得1996年,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陈耀先来做学术讲座,就是在电教报告厅举行的。活动结束,陈耀先走到电教楼外,还有许多人围着他追问各种问题。1997年秋之后,除非是特大型的学术活动,一般的学术讲座,都安排在光华楼101、102、202、203这样的教室举行了。当时,曹老师请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、银监会主席刘明康、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等人做的报告,都是在这些教室举行的。有一次,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易纲来做讲座。曹老师临时有事,委托我代他主持。会场选在202教室。由于会场爆满,我讲完开场白走下台,就找不到坐的地方了。作为主持人只能和易刚老师一样,整场站立。
1996年,曹老师组织成立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后,这些论坛,都是以中心的名义举行的。2011年,曹老师和他的弟子们发起设立了北京大学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,之后每年都会召开一次颁奖大会和年度“金融改革与创新高级论坛”。曹老师逝世后,整理他的遗物,我发现,120多期的论坛,每期都有录音带或者光盘,装满了三个大纸箱。现在,我已经把“经济与金融高级论坛”更名为“凤岐金融发展论坛”,每年不定期举办,同时继续举办年度“金融改革与创新高级论坛”,以缅怀曹凤岐先生的学术风范,推动中国金融学研究的开展和金融实践的创新。
1999年7月,我毕业留校,在光华楼四楼,也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。虽然只有7个平米,已经很满足了。第一次来办公室,隔壁的同事热情地和我打招呼,自我介绍说,他是会计系的老师,名叫项兵。光华不仅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学生,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教师。这些老师不管是否离开光华,都有非常好的发展。
留校第一年中国星配资,我和黄涛老师一起担任1999级本科生的班主任。当时,由于北大校园资源不足,所有人文社科院系的本科生,必须要到昌平度过第一学年。我们和同学们在昌平园同吃同住一年,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。这一年,光华本科项目有金融学、会计、和财务管理三个专业。金融专业以前叫货币银行学专业,99级第一次改称金融专业。三个专业共招生108人。加上后来转系的3位同学,一共111人。我和每一位同学都非常熟悉。20多年过去了,和同学们还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。
留校第一学年,我给不同年级的本科生开设了三门课程,分别是《货币银行学》、《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》和《投资学》。开始上课的时候,只有粉笔和黑板。我认真准备了教案。当时年轻,记忆力好,我基本做到了板书讲课都一眼不看教案。后来,我发现有的老师在使用幻灯装置。我就学着先把板书的内容打印在胶片儿上,课堂上再通过幻灯机投影。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打印的胶片。再之后,不记得哪一年,才开始使用PPT教学。
2000年,我开始为光华1998级MBA在职班开设《货币金融学》课程。2001年又开始为MBA开设《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》课程。98级是光华招收的第五届 MBA学生。中国的MBA第一批招生试点院校有9所,居然没有包括北京大学。这些学校在审批之前召开联络会议,也没有通知北大。曹凤岐老师私下听说后,主动赶到上海参会,在会上广泛散发材料,以理据争。终于,第二批试点院校,北大名列第一。
曹老师是北大金融学科的创始人。但是他自己是1965级的本科生。在文革期间,没能系统学习金融课程。1978~1979年,曹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了两年金融研究生课程,聆听了黄达、王传伦、周升业、陈共、安体富等金融财政大家的课程,打下了金融学教学和研究的坚实基础。1979年开始,他在北大开设《财政与信贷》课程。1983年,开始开设《货币银行学》课程。1989年,曹老师将新出版的教材取名为《货币金融学》。从那以后,《货币银行学》教材,逐渐就都改叫做《货币金融学》。
现在,金融学系有教师30来人,是光华最大的系。但1999年,我刚到金融学系任教的时候,全系只有六位老师:曹凤岐,刘力,于鸿君、姚长辉、姜万军和我。我应该是本校博士毕业直接入职,留校任教的最后一人。在我之后,光华基本上只招海归博士了。我一直自嘲,我就是孙山。当时,光华开始调整研究导向。我在原单位的副高职称也不被承认,只能从讲师做起。记得接替曹老师担任常务副院长的张维迎老师对我说,光华是没有铁饭碗的,要想长期留下来,必须要在英文的顶级杂志上发表 论文。我当时听了,感到一片茫然,压力很大。虽然当时我已经有十几年的学术发表经历,包括顶级中文杂志发表,但是,别说英文写作,遑论发表,我甚至还没有认真读过英文的金融学术论文,也不知道金融的Top Three叫什么名字。虽然转型是大势所趋,我本人也选择了积极转型,但这一代的本土学者(我本科是1981级)承担了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成本,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40年了,光华从一间水房到两栋办公大楼,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教师队伍不断壮大,学术水平不断提高,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优秀学子。这些成就的取得,是一代又一代老师,职工,同学和各界朋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在庆祝光华成立40周年之际,我们尤其需要铭记的,是厉以宁、曹凤岐等老一代光华学者,在艰苦的条件下创立学院,努力办学的精神与贡献。没有他们当年的辛勤耕耘,就没有光华的今天。在此,我想引用曹凤岐先生2005年7月写的一首诗,作为文章的结尾:
花甲有感
曹凤岐
六十花甲忆人生,追梦求真路难行。
股份改革点星火,证券立法铸章程。
创建学院基石奠,培育英才心血凝。
荣辱盛衰淡如水,洒向人间一片情。
2024年12月3日初稿
2025年1月16日修改
实倍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